闽东之光 | 陈健:诗人另一重精神层次的突围
诗人另一重精神层次的突围
——读汤养宗散文集《书生的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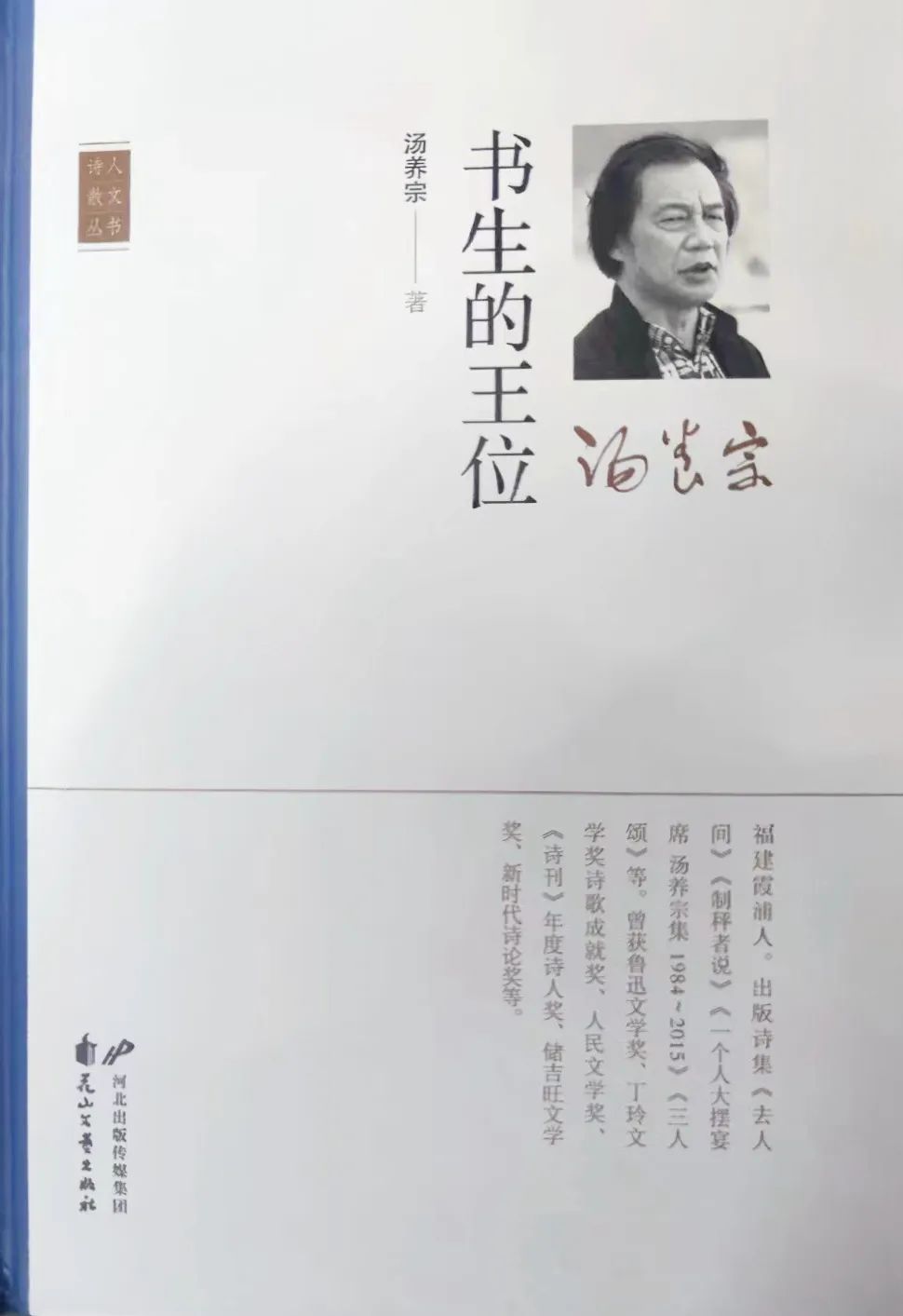
诗人写散文,在中外文学史上代不乏人,已形成悠久传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前赤壁赋》等,都是诗人创作的天地至文。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这一传统并未中断,而且诗人转向散文创作出现文名盖过诗名,或者诗文并举的情形也很普遍。冰心、朱自清、何其芳、李广田、徐志摩、朱湘、冯至等现代诗人均有独特而精美的散文作品,诗人写散文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特别是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人散文名篇。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布罗茨基的《文明之子》、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脑》、希尼的《舌头的管辖》、帕斯的《弓与琴》等,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散文名作。近期,汤养宗推出散文集《书生的王位》展示了当代中国“诗人散文”的独特艺术风采。

汤养宗的诗人散文一方面承担了诗人确立自身诗学理论和实践合理性与合法性的任务,同时也扩大了其诗歌与诗学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认为,“我们作为人在精神上也是由多重层次迭加在一起的人组合而成的。”这是人类精神的普遍规律,但在诗人那里又更加明显,因为“诗人多有一重天,在他们天才这一重天,与他们的才智、善良、日常生活中的精明智巧这一重天之间,还有一重天,这就是他们的散文”。在普鲁斯特看来,诗人散文既不是天才的结晶,也与世俗社会中的“才智、善良、日常生活中的精明智巧”判然有别,它是介于二者之间或独立于二者的存在。诗人写作散文时,是把“诗才暂时搁置一旁,暂时停止启用他从超自然、完全属于个人的世界中得到的形式”,但又不是彻底遗忘,因为这些散文“仍然让我们依稀想到那些诗情”。普鲁斯特这种把散文视为诗人的另一重精神层次的观念,其实隐含着十分深刻的人性悖论。人既是肉身性的存在,又是卡西尔所说的“文化动物”;既以肉身经验着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又以心灵体验着无限的文化和精神;既依赖世俗,眷恋红尘,又渴望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既热衷于向外部世界攫取而“沉于物”,又担忧自我内在灵性的消失而“溺于德”;既有来自对象和表象的感性冲动,又有对普遍本质和真理的理性诉求。正如养宗所道“我在另一首诗里说到我的身体就是我借以修行的一座寺院,宏伟,空旷,又寂寞”(《毫无胜算的事(代跋)》)。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汤养宗的诗歌写作看作“感伤的诗”,主要承载着诗人精神天空中那些感性的、主观的、无限的内容;可以把汤养宗的散文写作看作“素朴的诗”,主要寄托诗人精神天空中那些知性的、客观的、有限的内容。对于诗人而言,诗与散文是其精神世界中两种表意实践的产物,各有其实现诗人美学理想的效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理解自惠特曼以来那种拼命要打破古典主义所划定的诗与散文之界限的冲动,才不致被文学史上反复涌现的诗歌的散文化、叙事化潮流所困惑,才不会看轻拥有广泛创作群体的散文诗。而兼善两者的和谐境界,在某些作家看来,就是作家最大的幸福。正如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只有诗歌和散文的有机的融合,或者更正确地说,充满诗的本质、诗的生动的精华、清澄的气息、诗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的散文,才能是文学中最崇高、最动人的现象,才是真正的幸福。”事实上,散文与诗歌之间的边疆,已变得愈来愈具有浸透性──被现代艺术家典型的极大化精神特质统合起来:创造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的作品。养宗始终“认为只有多维的文字才能规约住多维的世界,才能开阔。认为唯如此文字在手上才会出现一种新的可能,才能应对心中的真实和世界的真实”(《一个逻辑怀疑者在一座山上的左想右思》)。

汤养宗在他的散文中提供了一种幅度更窄的体裁,一种诗人散文的更纯粹范例。汤养宗的诗人散文不仅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密度、速度、肌理,更有一个特别的题材:诗人使命感的成长。一般而言,它以一个包含两种叙述的面目出现。一种是具有直接自传性质,如《读书的地盘》:“人生的开悟处往往是一灯即明的暗室,而我的暗室就是这四处都是波涌之声的海底中”“内容与意义在我现在的年龄都是现成的,只有表现的手段才是永远的迷宫。在各式各样的迷宫中,建造者不同的手段显示了人与世界之间不同的精神关系”。另一种也具有回忆录的性质,要么是同行诗人《保重,我们再也上不了情人桥了》:“我一直想紧紧藏掖着几件事作为自己与伟雄之间的压舱石压在那里,不说也不提,任由时间上继续延长,相信它逐渐会成为一种势力,或者长出越来越旺盛的几缕心香”;《谁知道那是酒事或者诗歌,与俞昌雄的或酒或事或诗》:“作为读者,可以感受到他与自然那种神秘的亲近感,那种贴近的力量,而这,正是他作为诗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诗事,酒事,一场欢乐英雄们的事》:“我有一句诗,叫‘坐在第一排的诗人都不是好诗人’”。要么是被爱戴的亲人,如《生命的屋顶》:“人生命中最高的地方便是自己的屋顶,因为那是作为我们父母的象征而存在于这个家的高度”。向别人致敬,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于粗俗的自我主义。在向重要楷模致敬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
汤养宗的诗人散文,更主要的还是关于做一个诗人。而写这样一种自传,写如何成为一个诗人,就需要一种自我的神话学。被描述的自我,是诗人的自我,日常的自我(和其他自我)常常因此被无情地牺牲。汤养宗的很多散文作品,都是对诗人自我的描写:“我知道,一些常识性的标记是我此生永远关切,却又永远模糊的地带”(《我是我自己身体的异乡客》),“写作,正是一个书生一次次在精神上的登基”(《书生的王位》),“看住我并让我信以为真的,是时间中积攒下来的那些看去似有似无的一点一滴的生活依据。而且有了拒绝,拒绝一切外来的可能破坏我这种心境的喧嚣”(《我已在自己的地方渐渐老去》)。汤养宗诗人散文总是挽歌式的,回顾式的。仿佛被描述的对象按定义来说是属于消失的过去:“万物会悄悄地把空间让出来,并相信你正在守约的这一切,让我们活着的这个世界有了可靠的信条,恒定,道义,以及可以继续延传下去的理由”(《生命的地图》)。
汤养宗的诗人散文是激情的自传,所有散文都是为狂喜辩护,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诗学。做一个诗人,即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高昂的存在状态。汤养宗散文中具有一种跟他诗歌中同样的情感高扬的特质:没有任何当代作家可以使我们如此接近一种崇高的经验。就像茨维塔耶娃指出的:“没有人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有人两次踏入同一本书吗?”
来源:闽东日报通讯员 陈健
编辑:陈娥
图片来自一个人大摆宴席
责任编辑:陈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