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福地·诗画蕉城|谢宜兴:石堂有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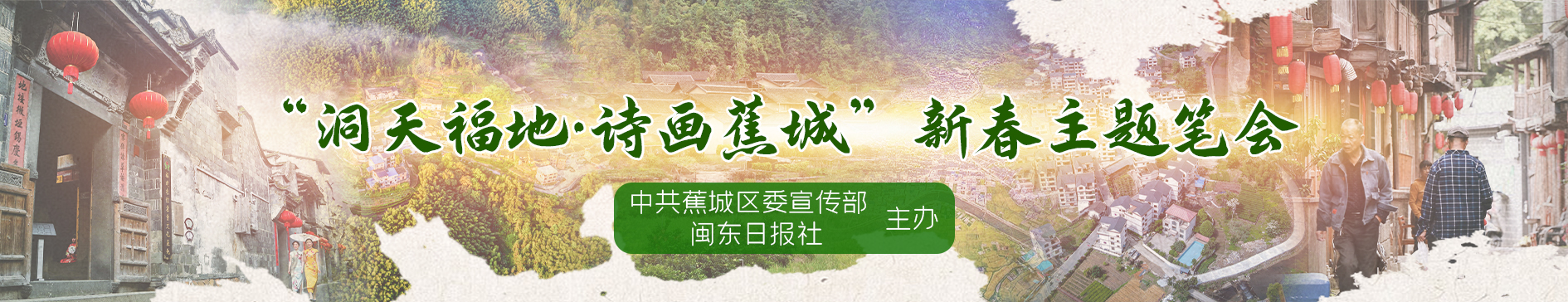
蕉城虎贝镇,有村叫“梅鹤”,但凭这一名字,便足以令人神往。
“梅鹤”二字,自然让人想起那个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诗人林逋。而梅鹤村名的由来,还真是源自于他。

梅鹤春色 刘岩生 摄
梅鹤村和相邻的文峰村,一南一北,原来都叫石堂,古有“石堂三十六村”之说,至今已近千年历史。因梅鹤村民大多姓林,称“石堂林厝”;文峰村民黄姓为主,称“石堂黄厝”。明末清初,因敬慕同姓和靖先生“梅妻鹤子”的淡泊人生与隐逸情怀,“石堂林厝”将村子更名梅鹤。而“石堂黄厝”看重村前文笔峰,村随山名改为文峰。
有观点认为林逋终身不娶,只是佳话而非事实。甚至指其后人分别在奉化与日本,曾经会师杭州寻根孤山。其实,“梅妻鹤子”已成一种文化符号,深究林逋侍梅伴鹤前是否娶妻生子,或者身后是否按民俗过继孩子接续香火没有意义,但他确实被美化了,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隐者。著名学者夏承焘也认为,“林逋不是完全遗世绝俗的人”。
可我更喜欢以出世情怀入世生活的林逋,那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林逋,也是“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难平”的林逋。
因此,对于梅鹤之行,我怀有期待——它是林逋的诗人情怀穿越时空的投射之地;在梅鹤与文峰还没有从石堂分开之前,还是南宋诗人、理学家、教育家、天文学家陈普故里。
在初春的轻阴薄寒中,我们来到梅鹤。车子径直开到村西的花桥旁,当地村干部指着墙上的村庄全景图、导览图和民国时期的县域地图,向我们介绍石堂的变迁与梅鹤的历史。绕村而过的九曲唐溪像是配合解说,从花桥下静静西去仿若流年。

梅鹤花桥 李在定 摄
花桥是宁德境内最古老的石拱廊桥,原名登龙桥、沉字桥,始建于北宋崇宁五年,清乾隆四十三年重建,更名花桥。有“宁阳第一桥”之誉,可以说是梅鹤村的形象大使。
而这,却是源于一个梅鹤人津津乐道、经久不衰的传说:宋大儒朱熹与后学陈普在花桥上的“千古唱和”。
相传宋淳熙年间,朱熹路过石堂,渴饮泉水觉有墨香,预感此地日后将出大儒。一时兴起,在建造中的登龙桥亭尚未架起的木梁上,写下“紫阳诗谶石堂名彰千古”,墨渗木中,刨之不去,“沉字桥”因此得名。七十年后,当地学子陈普与友人同游此桥,见桥屋梁上只有上联,灵感忽至,对上“玄帝位尊金阙寿永万年”,上下联对仗工整,成就了与朱文公穿越时空的“共同创作”。
花桥两头有两座宫庙,北端是林公宫,南边是东岳宫。林公宫大门紧闭,我们穿过花桥来到东岳宫。
东岳宫始建于元代,原是石堂谢家祠堂。明永乐四年,石堂谢霖考中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庶吉士虽非官职,却是皇帝身边近臣,进入内阁的“跳板”,如张居正、曾国藩都曾是庶吉士。因此,传说是谢家出仕徙居别处,也有说是后来蒙难迁往他乡。总之,最后弃用的谢家祠堂被改成了如今的宫庙。
东岳宫也是梅鹤村引以为傲的一处风景。建筑由门楼、敞廊、偏房以及三座并排的大殿组成,规模不大,但门楼建筑颇具特色,四层如意斗拱叠涩出檐。叠涩是一种古代砖石结构建筑的砌法,逐层堆叠,传递负荷,增加美感,多层叠涩拱常见于砖石塔等砌筑,在门楼中不多见。还有宫门前的抱鼓石及门枕石系木质漆面,更为罕见。
集佛、道、儒三教于一体是东岳宫最特别之处。踏进宫门,但见三间大殿不仅供奉东岳大帝、温、康元帅及陈靖姑,如来佛祖及观音、弥勒,还有朱熹、陈普。
在乡下,老百姓把佛、道混同是常有的事。你问一个烧香磕头的老婆婆,她会告诉你,佛就是菩萨,菩萨就是神仙,他们都是保佑平安发财的。
民间信俗中,为神者必是好人。在福建,林默娘成了妈祖海神,陈靖姑成了临水娘娘,林亘成了林公大王,他们同样都是为民除害、救苦救难,得到百姓崇拜、朝廷赐封。这种看似粗粝的信仰形态,实则有着潜在的世俗引导与价值指向。
老百姓求神拜佛讲求实用。不管是佛是道,“灵验就拜,不灵拜拜”。求运求财、祈福消灾,在他们眼里神是万能的。不求灵魂救赎,但求现世安乐,这种信仰态度很有韧性,它是正统宗教的异数,却是乡土文化的常态。
因此,对于梅鹤东岳宫里儒释道融合共处,我一点不诧异。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把乡贤陈普也作为一尊神供奉其中。
陈普,字尚德,号惧斋,宋淳祐四年出生于石堂(今文峰村),世称“石堂先生”。在一首就以《石堂》为题的诗中,他写道:“仙佛人言是一家,好分半席共烟霞。”这句诗在东岳宫里读来,仿佛预言。
陈普青年时曾就学于浙东崇德书院,受业于韩翼甫门下,算是朱熹的三传弟子。把朱熹和陈普供奉在一起,促成他们从沉字桥上的隔空唱和,到东岳宫里的同室交流,倒是一次难得的成全。
我想,石堂乡人把“石堂先生”作为神来供奉,那是对其智慧灵性的钦佩,品行节操的景仰,学问功业的敬重,求真精神的尊崇。当然,也是一份乡情的重塑再造——
陈普七岁时,于田间嬉戏,见白鹭飞止,即兴《咏白鹭》:“我在这边坐,尔在那边歇。青天无片云,飞下数点雪。”一个少年如此的想象力与诗才,其慧心与灵气让多少诗翁望尘莫及。
南宋灭亡后,元朝三度诏聘欲起用陈普,可他坚辞不就,以宋遗民自居。“白云生远岫,明月照清秋。不问尘世事,免撩世俗流。”《山居》的日子,高洁自守。“山河千里远,故国几多愁。……丹心昭日月,誓死不言休。”《冬日感怀》故国,怀念之情、捍卫之心跃然纸上。
陈普学问精深,著述甚丰。数百卷作品今多散佚,仅存《石堂先生遗集》等二十余卷。宋亡后,他先在石堂仁丰寺设馆倡学,招徒课艺。6年后离乡,兴办政和德兴初庵书院,受聘主讲于建州云庄、福州鳌峰、莆田勿轩庄等多家书院。慕名求学者不绝于途。培养了韩信同、余载、黄裳、杨琬等一大批理学名士。
经学之外,陈普让我惊为天人的是其天文学的造诣。他著有《浑天仪论》,研制出聚铜铸刻漏壶,为当时最精确的计时器,世界最早的钟表雏形。一天的误差在20秒内,从宋末到明末,推广使用了近400年。一个书生干了一个工匠的活,一个诗人校准了一个国家的时间,一个理学家完成了一个天文学家的使命!

梅鹤春色 柳德甫 摄
陈普对石堂感情深厚,三十年流寓在外,写下许多怀乡诗作。晚年思念家乡,作《归去来辞》《寄园洲》等。元延祐二年病逝于执教十八年的莆田,归葬石堂山。他爱乡,乡人也以他为荣,文峰村为他立祠,东岳宫奉他为神,也算是应验了他在另一首题为《石堂》的诗中所言,“终当结屋此云栖”。
我相信,一个把先贤当作神来供奉的村庄,必将激励后人而贤达辈出。一个有神的村庄,自会得到神光照耀而门庭焕彩。
离开东岳宫,我们接着参观了梅鹤村的“石堂传统文化展览馆”和文峰村的环水宫、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集训地。由于时间关系,“石堂八景”只能在诗中想象,梅鹤、文峰的古建筑群只能在图中欣赏,甚至陈惧斋祠也未涉足,难免遗憾,但也算留个念想给下一次。
走过梅鹤,除了村名,见不到与林逋有关的丝毫展示,好在东岳宫里见到了陈普先生,一种欣慰让我觉得不虚此行。
来源:闽东日报·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谢宜兴
编辑:邱祖辉
审核:刘宁芬 林珺
责任编辑:邱祖辉
(原标题:洞天福地·诗画蕉城|谢宜兴:石堂有神)
